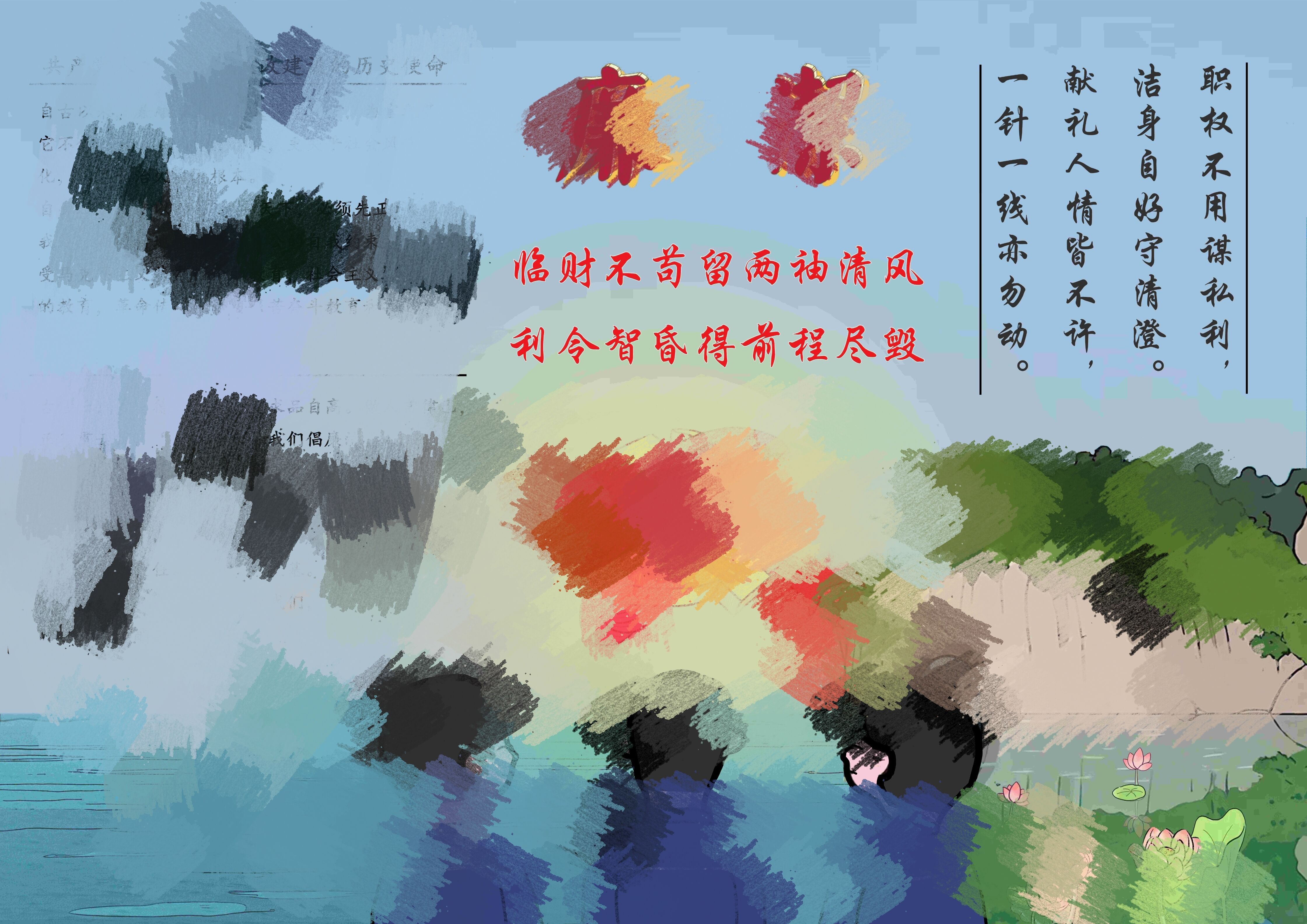2024.11.10
前不久我去了一趟凌云,作凌云乡间词曰:“细雨凌云,雾伺群山。三千亩桑田育白蚕,平怀村果酒满杯盏。东风阵阵,闻此间,百啭千声画眉珍。苍云滚滚,见此峰,腰间驻起三两屯。澄碧河宽,暮秋清寒。见几家夫妇相伴返,得致富强民好发展。”
大概我今年的夏末和一整个秋天都是在辗转中度过的。六月从阳炎如火的沈阳毕业回昆明。八月从四季如春的昆明,辗转到广西群山里一个之前从未听过的小城-西林。又来来回回辗转于百色,桂林,西林。
诗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去年我上课走神,只记得个读音,考试时就硬着头皮写了个“一之日碧波”上去。后来才知道“觱发”说的是风的寒冷。十一月的百色有时还是会像夏天般热烈。我感觉我还是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去年我在铁岭实习,有时候傍晚回家,我会突然理解为什么东北的小孩子在冬天往往下午三点放学。天冷天黑早是一个原因,但或许还有一个原因是:看到暮色挂在泛白的天边,感受着冷风打在脸上,或许小孩子会在一瞬间感到人生的荒谬与虚无,便再也无法克制着自己去寒窗苦读了吧。
我一直喜欢雪,想看它飘起,又簌簌地落。或许这和我是个南方人有关,在故乡的十九年里,冬天不见雪是常事。人们总是期待着陌生的事物,它们在幻想中被赋魅,直至流光溢彩。可现实总是没有这么多色彩,我早就在无数多的影视作品中见过了雪。它们在我来东北前,构成了我想象中的某种色彩之一,将雪描绘的愈加神秘。可我却对在东北的第一个冬天并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一些孤单与害怕。
最近我迷恋上了吃火锅,这是一种简单的烹饪方式,只需要洗好菜,再把底料扔进水里煮热就够了。或许在上万年以前,在人类的祖先学会了用火烤食物后,用热水煮食物也便已经被尝试了吧。这种古老的烹饪方式能够给予在寒风中吹了一天的人一种亘古的感动,流连许久不散。不过我经常吃的满嘴流油,希望不要因此变胖。
唉,胖瘦高矮,无数的特征排列组合构成了一个人,世界也因此而参差多态。可为何往往分出个高低贵贱来呢。记得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还有些年轻,和我聊起工学院,说十几年前,校门口常常有车一停停一天,在车窗前放个饮料瓶,有的放矿泉水,有的放宏宝莱。我问这是什么意思,他嘿嘿一笑,说是为了给女学生标价。
老师也聊过她上学时,工学院女生宿舍楼下只有一个电话亭,总是一到傍晚就排上满满的队。大家在寒风中披紧着大衣,等待着打电话。我问老师为什么,老师说有打给父母的,但更多是谈恋爱的青年,异地恋苦哇,接着就笑着说同学们最好谈个同城恋爱,不用大晚上的吹风。
风吹雪,是最叫人孤单的景色。走在人行道上,来往的行人往往都搂紧了大衣,匆匆而来,又匆匆离去,似乎在防范着灵魂被暮色吸了去而变得虚无。我已经无数次地走过了校门口外这条路,例如第一次来大学时,我站在门口和母亲挥手告别;例如有天军训结束时,知道了有个朋友去世,我打着伞往家走,记得有辆白车车窗前摆着一个哆啦A梦。例如大二时有天我很难过,就在路上打电话,打给妈妈,却说不出来什么。
此时此刻,我知道:我正走在未来的回忆之中。
我想,今晚回家煮上一锅火锅吧,想看白气咕噜咕噜,从那圆形的红色中腾腾涌出。
2024.11.10